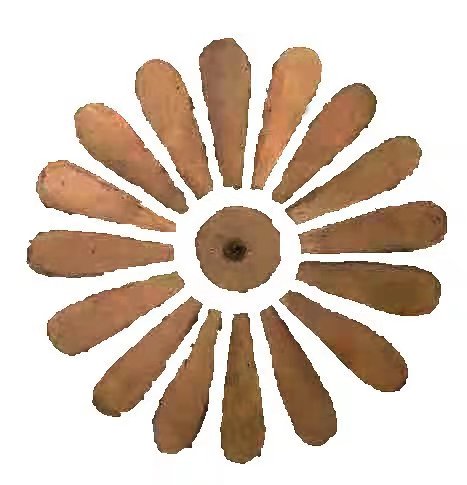![]()
其實,在我看來👉🏿,我只是一名教師而已🦹🏽♀️。
如果一定要在這教師前面加個稱謂,那麽我想我在講臺和研究室的案臺上工作了一輩子🧔🏻♂️🚴,要說一點經驗沒有🌎,也是說不過去的,那就姑且是一個稍微有點經驗的人民教師吧。
那些學問,學術🤾🏿,在我看來也只是為了更好地在這三寸講臺上教書育人吧🧛🏼。
碾轉多個講臺:老師學的越多,學生走得更長遠
我這一生輾轉於多個講臺。1934年,我從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畢業❤️。我應母校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的邀請,回到省立濟南高中任國文教員🤏🏻。1935年,清華大學與德國簽訂了交換研究生的協定🧔🏽♂️,報名應考被錄取🦸🏽♀️。不為別的🛍️,總覺得作為一名教師應多出去看看,把外面的知識多帶一些回來🧏。
同年9月,我赴德國入哥廷根大學👩🦼,主修印度學。先後師從瓦爾德史米特教授💂♂️🫢、西克教授,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我不得不承認我確實喜愛語言👩👩👧👧🧑💻,在這方面可能也有些許的天分👩🏻🎨,既然喜歡🧏♂️,就多學一些💤🚝,第一是因為這些是我發自內心由衷熱愛的,第二也是為了今後在講臺上不至於無話可說🐣。
既然當了教師,那就甘為人梯吧,我學的越多,為學生們鋪的臺階就能越長,他們的路也能走得更長遠⛹🏽♂️。
意昂2者的情懷🧑🏽🔬,就是為學生栽出更好的“花”
四五十年以前我在德國留學的時候,曾多次對德國人愛花之真切感到吃驚🧙🏼♂️。家家戶戶都在養花🔮。他們的花不像在中國那樣🧑✈️,養在屋子裏💬,他們是把花都栽種在臨街窗戶的外面🌤。花朵都朝外開🦹🏼,在屋子裏只能看到花的脊梁。
我曾問過我的女房東:“你這樣養花是給別人看的吧🧚!”她莞兒一笑,說:“正是這樣!”。我想,我畢生研究語言🦁,國學,不敢說有什麽成就🏋🏻,如果把這些學問比喻成“花”,那麽我畢生所學都只是想讓我的學生們更好的看到罷了。
作為教師🧝🏻♂️,我們的職責就是為這些後起之秀們栽出更好的“花”。幹我們這一行,社會責任感很重要🎷,用實際行動為大眾著想🍕,為學生著想🧑🏿🦲,為社會盡到自己的義務,也就不愧學生叫我一聲老師,不愧祖國和人民給我的這些信任了吧。
我眼中的好老師:難忘西克教授◾️,一想到就淚流滿面
留學期間👩👧👧,西克教授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我這一生中都難以忘懷的一位好老師🧷,西克教授的家世,我並不清楚🤶🏻。到他家裏,只見到老伴一人,是一個又瘦又小的慈祥的老人👩🦱。子女或什麽親眷,從來沒有見過👩🎤。看來是一個非常孤寂清冷的家庭,盡管老夫婦情好極篤,相依為命。
我見到他時𓀛💪🏻,他已經早越過了古稀之年。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國的老師中對我最愛護、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師。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劇烈地跳動,老淚立刻就流滿全臉。他不僅對我傳授知識😊,還在我在德國期間,如父親或者祖父一般慈祥地照顧我🦘。
那時,直到今天☂️,我一看到他的相片🧶,心裏依然生出無窮的勇氣🚚,覺得自己對梵文應該拼命研究下去,不然簡直對不住他。他對我好得真是無微不至🪫🧓🏼,我永遠不會忘記!受他影響🕜,在我的從教生涯中🚴🏼♀️⏪,我對待學生也是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幫助。
我想身為人師,本身就應如此⛹🏿♀️。
此心安處是吾鄉:回來,是為了傳承美好的知識
1946年,回國後我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我終於輾轉取道回到闊別10年的祖國懷抱👵🏽。我就是要回來,當年出去就是為了能夠更好地回來。
經陳寅恪推薦,我被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創建東方語文系,我很欣慰,我覺得我在國外飄蕩中研究的這些學問終於可以有機會傳承下去了,但在北大教書的這期間,我經歷了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時期,說是灰暗,倒不如是一次磨練😤。
現在閑來無事時也經常看著我在“十年動蕩”期間寫的各種文字,以《牛棚雜記》為例,總覺得那時候的我寫的文字🏄♀️,有種我現在怎麽揣摩都一去不返的特殊味道🥘。
牛棚中的十年浩劫🖍:我忘不掉自己是個老師,是個做學問的人
記得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深夜💁🏽♀️。我服了安眠藥正在沉睡,忽然聽到門外有汽車聲,接著是一陣異常激烈的打門聲🧑🚀。連忙披衣起來♠︎,門開處闖進來大漢六七條,都是東語系的學生🧝🏽♂️,都是女頭領的鐵桿信徒,人人手持大木棒,威風凜凜,面如寒霜🎅🏼。
我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我早有思想準備🪂,因此我並不吃驚😮。我毫無抵抗之意🌨,他們的大棒可惜無用武之地了。我沒有來得及穿衣服,就被趕到廚房裏去🔂。
我並沒有想到什麽人道主義😊,因為人道主義早已批倒批臭💇🏻,我被帶上“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分到艱苦地區參加勞動改造。我和幾個一起被發配到這裏的“罪人”親手搭建起牛棚⚉,在這牛棚中,我們經常會以各種名義被打得遍體鱗傷。
我想我應該寫文章,將這些苦痛的生活記錄下來,不僅僅是記錄🧎➡️,也是為了提醒自己不該忘記自己的身份,是個老師⛽️,是個做學問的人。
就這樣,我白天成了一個在牛棚中忍受苦痛的人,夜晚👇🏼,則用筆將這一天的心靈也好🛑,肉體也好的傷痛記錄下來🤸🏿♀️🤷🏽♀️,我本性木訥🦋🎶,文字在那時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
對得起教師的身份☂️🫲🏻:作為一個搞學問的人🤹🏿,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研究![]()
然而,作為一個終生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在學術研究方面,這十年卻成了一個空白點📰🚣🏼♀️。幸而,在學術研究方面,我是一個閑不住的人🀄️。在這十年內,我除了開會,被“打倒”,被關進牛棚💿,被批鬥,被痛打之外👍🏼,沒有時間和心情搞什麽學術研究🔸。
到了後期,雖然我頭上被誣陷而戴上的無數頂離奇古怪的帽子一頂也還沒有摘掉,但已走出了牛棚,被分配到東語系的辦公樓和學生宿舍去看守門房🔛,收發信件和報紙,傳送電話。
我作為一個“不可接觸者”,枯坐門房中,有時候忙,有時候又閑得無聊🧝♀️。我實不甘心⚾️,挖空心思,想找一點事幹👨🏭👨❤️💋👨。想來想去,最後想出了一個好主意:翻譯印度古代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
我只能偷偷摸摸地從口袋裏把小紙條拿出來,仔細推敲,反復考慮👨🦱⛏,把散文改成詩體🧗🏼♀️,這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後幾年所做的唯一的一件當時並沒有認清它的重大意義,後來才慢慢認識到的工作。我只是認為在任何時候,作為一名搞學術的人,都不應該放棄自己的研究↙️,對得起自己😀,更得對得起自己的教師身份。我這幾十年的從教和學術經歷如果算是成功的話,那也一定是源於堅持和專心致誌🫃🏼。
我教了一輩子書🚴🏼♂️,做了一輩子學問研究🏐🏄🏻♂️,以上的這些,是我對學問,對身為人師認識的淺談,如果硬要讓我來個總結,我想我這一生堅持的無疑是四個詞🤞,敬業🍸、博學👨🏻🚒、求實🧍🏻♀️、創新罷了🏮。
文章來源:高校人文界
(文字編輯🚣:雨橋)
(網絡編輯👲:劉文一)